小城交错纵横的路灯电线上总会密密麻麻地站立着成千上万的燕子


傅汉洵,1941年11月生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丁宜市,后迁往先达,籍贯中国广东潮阳海门镇。1959年12月底启程回国,1960年5月加入广东省羽毛球队。退休前任中国羽毛球国家青年队副总教练、广州市体育局羽毛球队总教练等职,培养出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林燕芬、谢杏芳、张洁雯等多位羽毛球世界(奥运)冠军。
口述 | 傅汉洵
撰文 | 朱婷
“
听闻广州又新开一家餐馆,印尼风味的饭菜和糕点颇为正宗,我心痒难忍,准备约上老友一同去品尝。
此生无论在何处,闭上眼睛,童年时先达小镇的样子就在眼前;印尼饭菜和糕点香甜的味道,依然在口中蔓延……
先达“奇观”
先达,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第二大城市,是我成长的地方。著名的印尼民歌《星星索》《宝贝》都诞生于先达附近美丽的多巴湖,由先达华侨翻译传到了中国。
先达虽不临海,但海拔高,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由荷兰殖民政府规划而成,有着大片的橡胶、油棕、剑麻园;还有火车站、足球场、公园、游泳池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达的商业已颇为繁华,街道两边商铺林立,由于华侨众多,大街旁的横街多以中国城市为地名,被称为“福州街”“南京街”“上海街”……
白天,街道喧哗热闹,我穿梭其中寻伴玩闹,吃着零嘴,耳边尽是“先达国语”(印尼特色的中国普通话,至今在全世界只要听到讲这种话者,十有八九就是先达人)、潮汕话、客家话、闽南语……夜晚,店铺关门,街道便安静了下来。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每年年初的某段时间里,每到黄昏,小城交错纵横的路灯电线上总会密密麻麻地站立着成千上万的燕子,叽叽喳喳黑压压的,仿佛电影开场前合拢的大幕,甚为壮观。第二天一早,小城“醒”了,燕子也便成群起飞,四处觅食,到了傍晚再回来。如此反复,是我心中旧时先达的一大“奇观”。

▲傅汉洵在印尼的留影。
多年后再问先达的家人,燕子是否还如期而至?家人答说,这“奇观”早就不在了。原来燕子和我们一样,也离开了先达。如今印尼的燕窝依然闻名世界,燕子应该没离开印尼,只是因城市开发搬到更远的悬崖峭壁筑窝了吧。
1950年,我们一家刚搬到先达时,暂时租住在友人家一间小房里。1953年,父亲另起炉灶,在先达“弟波尼格罗街1号”创办了“新光印务公司”。我们便搬到了公司居住,那是一座由锌片、水泥、木头制成的厂房,前面用以办公,中间用以印刷,我们一家人住在后面——用木板隔开的几间小睡房里。
白天父亲工作繁忙,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8人,常给我们煮家乡菜和印尼菜吃。早上急着上学,母亲还能给零用钱让我们在外面吃炒米粉、椰炼糯米饭、“炸香蕉”等。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无忧无虑,即使当时印尼华侨生存环境时有动荡,因有父母的共同支撑,我们家中总是温暖的,充满了欢闹声。
婉拒苏迪曼先生
新闻上说,受疫情影响,原定于今年5月在苏州举行的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将延期,让人不禁心生遗憾。
犹记得2005年12月9日,国际羽联在吉隆坡宣布,2009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将在广州——这座我居住的城市举办时,我激动得一夜未眠,深感此生与“苏迪曼”3个字的缘分又续上了。
早在1958年下半年,17岁的我代表先达参加北苏门答腊省羽毛球赛。在男单决赛现场,我与代表棉兰市的华侨青年黄广源相遇。经过激烈的比拼,我输掉了这场比赛,却与对手一同,获得了前来观赛的迪克·苏迪曼的青睐。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印尼羽毛球之父”刚刚带领印尼羽毛球男队创造了历史,击败了3届汤姆斯杯得主马来亚队,第一次捧回汤姆斯杯,让印尼举国欢腾。
作为先达籍人和印尼羽协的创始人,苏迪曼当时正打算回乡寻找种子选手。他看着比赛的我们,面露喜色,急着向先达市羽协主席询问两位年轻选手的情况。该主席指着在旁陪着他的先达市羽协副主席——我父亲傅高宾对他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个是棉兰的,另一个高个子男孩就是傅先生的孩子啊!”
苏迪曼惊喜不已,表示希望带着我们俩到雅加达,与印尼国家羽毛球队一起集训,好好培养。这样的邀约对于当时的任何一个羽毛球运动员,都极具诱惑。但父亲缓了缓委婉地说,需要征求我的意见才能决定;并在第三天为苏迪曼送行时婉言谢绝了。
事实上,直到1965年后,我才获悉此事全部过程,也才知道父亲当年苦苦思虑了整晚:一方,是儿子对羽毛球的热爱与充满希望的未来之路;另一方,是祖国的需要以及拳拳爱国之心,他内心纠结却有了倾向。一年后,果如父亲所愿,我回了国,加入广东羽毛球队,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羽毛球事业腾飞的全过程。我从未质疑父亲当日的选择与爱国之情,而今想起,更是佩服他的远见。
可贵的是,苏迪曼先生爱才心切,虽被委婉拒绝,却主动派出当时印尼国手李宝灿赴先达,给我们辅导了1个月;随后还同意我们跟着李宝灿,从棉兰乘机经雅加达到中爪哇省继续训练。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乘坐飞机,更值得铭记的是,当我们抵达雅加达走出机舱,就看到了专程来接机的苏迪曼先生。他身材不高,带着眼镜,气质斯文果敢,总是笑容洋溢,眼神坚定而明亮……
前辈们的帮助与指导,奠定了我的羽毛球基本功,将我真正引入职业羽毛球运动员之门;他们对羽毛球的纯粹热爱与对后备人才的关爱,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里需要你”
早在回国前几年,我的脑子隐约地就有“作为长子,肯定是要回国”的念头。在苏迪曼向父亲提出邀请的当晚,父亲便立刻向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的马领事询问国内是否需要青年羽毛球人才,并介绍了我的情况。在得到肯定回复后,父亲将我送回国的心情便更加坚定了。

▲1959年,傅汉洵(前排中)回国前与印尼华侨同学们的合照。
1959年,父亲正式提出让我尽快准备回国,并开始准备我的行李。“你回中国吧,回我们的家乡广东,那里的羽毛球队需要你,你以后可以代表中国打球!”他对我说。我虽觉得有点突然,心里其实早有准备,也立即答应了父亲。
1959年12月29日,我乘坐“芝丽华”号客轮,在棉兰市的勿拉湾港起航回国。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前来为我送行。我的舱位是大通铺,在船舶的最底层。上船后,我立即进舱放下行李,又跑到甲板上,挤在人群中寻找亲人们的身影。我找啊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便拼命挥手叫喊;眼见着,他们也一样,在几千人的人群中拼命地向我挥手呼喊,即使根本听不清彼此到底在喊什么……
 ▲傅汉洵回国前与家人的合照。
▲傅汉洵回国前与家人的合照。
客轮缓缓出港,我也就这样离开家独自回了国,不知何时才能与家人相见。我心中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悲凉感,潸然泪下。
1960年1月5日,经过几日海上的漂泊,甚至遭遇了海上风暴,“芝丽华”号总算有惊无险地驶入香港水域。经过罗湖桥中线后,喇叭里传来了熟悉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首歌,早在先达我就耳熟能详了。而那一天,在这样的音乐声中,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我知道,我回来了,我带着父亲的期望,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
在《歌唱祖国》的音乐声中,我们自觉地排成队伍,跨过了罗湖桥……
“
广州的天气四季如春,正适合打羽毛球。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座现今的“羽毛球之都”、世界羽毛球顶级赛事“大满贯”第一城,差一点儿就要失去羽毛球队。
彼时19岁的我,带着父亲亲手置办的行李与2副羽毛球拍,怀揣着为国争光的梦想和忐忑的心情,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
人生第一场 0:15
我是10岁左右开始打羽毛球的。在此前,就常跟着父亲到韩友羽毛球场,看大人们打球。那是一个露天羽毛球场,停电时,工作人员会点上煤油汽灯,并挂在球场四边的柱子上。那个煤油汽灯头很特别,是网状的,点灯前要先打气,现在似乎再也见不到了。
在场上看久了,我和几个小朋友跃跃欲试,开始捡大人打坏的旧球打。放学后,我就拿着两面都是光板的乒乓球拍打羽毛球。一段时间后,我找了一块长条的木板,在上面画出近似羽毛球拍的轮廓,锯成了一个木板羽毛球拍,打起来更过瘾。再后来,父亲见我真的喜爱羽毛球,便给我买了一把普通的球拍。
后来,我的“野心”越来越大,与小伙伴们一同找到一家工厂外的闲置平地。经得老板的同意后,我们便自己动手,插上竹竿、挂上捡来的旧球网,挖出线沟、用小石子填充进去,再用泥土填缝压平……做出了特制的球场。每每放学后,我们都会酣畅淋漓地较量一番。
在我接触并爱上羽毛球的那段时间里,世界羽坛风起云涌,以黄秉璇、庄友明、王宝林等华人选手为代表的马来亚国手们,利用亚洲人快速灵活的特点,使得羽毛球运动由慢而潇洒,转向快且凌厉,一举打破了欧洲对羽毛球运动的统治。从1949年起,马来亚连夺了3届汤姆斯杯冠军;从1950年开始,连续8届斩获全英羽毛球男单冠军……

▲傅汉洵年轻时在球场上。
这在当时的马来亚,乃至海岛对岸的印尼掀起了羽毛球运动的热潮。当对岸的马来亚举办重要赛事时,印尼苏岛的球迷还会乘船渡海去观赛。侨社也乐于举办各类羽毛球比赛。1953年5月,先达侨团为了庆祝“五四”青年节,组织学生进行羽毛球比赛。在父亲的鼓励下,12岁的我参加了第一场正式的羽毛球比赛。
0:15,第一回合,我就被“剃了光头”。第二回合,我奋力拼搏,但最终也迅速败下阵来。我不服气更不气馁,对手年龄比我大很多;而1年前,我还在拿着自制的羽毛球拍与伙伴在工厂外的平地上练习。
在后来的数十年里,我打了数不清的比赛,有赢有输,却都不如这场印象深刻。我的羽毛球赛事起点定格在了印尼先达市的一个户外的羽毛球场上,我的未来定然在更高的领奖台上。
羽毛球队“保”住了
1960年一回国,诸事定妥后,我第一件事便是骑着从印尼带回来的单车,到当时的广州体育馆寻找羽毛球队。
那是一座具有浓郁苏联风格的建筑,有巨石廊柱、宏大的半圆形主体穹顶,据说是当时北京体育馆之后的全国第二大体育馆。正在训练的广东羽毛球队教练和队员们居然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看到他们训练时的投入与激情,我无比激动,深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在心中萌发,急切地想要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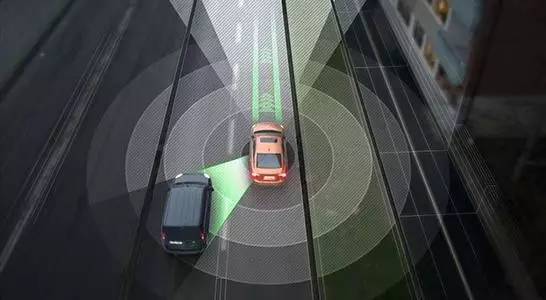
▲1960年广东羽毛球队男队员合影。
可当时国家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体育系统正面临调整,各省市区正削减专业运动员的数量,广东羽毛球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中。我很失落,为了心爱的羽毛球回国,在这么美好的体育馆和训练场上,还有这么多高水平的队友,却没有了球队,我不知道梦想该如何去寻。
焦急忐忑煎熬下,我们坚定信念,不愿放弃希望,依然坚持训练。到了5月的一天,终于传来确切消息,广东羽毛球队保住了!我心中狂喜,回到华侨补校后立即写信,告知在印尼的家人,与他们分享我的喜悦。
从此,我正式成为广东省羽毛球队的一员,开始了全新的羽毛球生涯。
饿着肚子冲击世界冠军
球队保住了,如何吃饱饭却依然是一个问题。我们运动员每月的伙食定额比普通市民高,但在大运动量的训练下,饥肠辘辘是我们常要面对的状况。听闻糖厂有丢弃的蔗渣可以提供糖分,我们派去了部分队员,好不容易“抢”了些蔗渣回来。
省市领导也非常重视我们的伙食,经过协调,广州三元里人民公社答应向我们球队供应一部分蔬菜。于是每周三,我们男队员总要骑着自行车或三轮车轮流运菜。苦瓜、节瓜、丝瓜、通心菜……有什么算什么。运菜回来擦把汗,喝口水,便继续投入训练中。
在那个时候,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着的不仅是梦想,更是国家的期待。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朱德、贺龙、董必武、李富春等中央领导都曾在春节期间来到广州。1961年春节团拜会结束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观看了羽毛球比赛,并饶有兴致地与羽毛球运动员们聊了起来。在得知广东、福建两队的主力球员主要是印尼归侨后,贺龙表示:“印尼队可以拿世界冠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3年之内,我们的羽毛球要赶超世界水平!”
3年,日子紧迫,我们的干劲更足了。后来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我以“饿着肚子冲击世界冠军”总结了过去的那段日子。这个说法被广泛引用,还被队友侯加昌加进了他的自传里,可见大家的心中都对那段日子记忆深刻。
以出色的发挥致敬偶像
 ▲傅汉洵年轻时。
▲傅汉洵年轻时。
1964年,印尼连续三次夺取汤姆斯杯成功,一时风头无两。同年,他们派出了国家羽毛球队再次访华。队伍中有陈有福、翁振祥、乌南、汪百胜,都是刚刚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选手;女选手则包括了米娜妮和莱诺等,可谓印尼访华以来实力最强的队伍之一。
我激动万分,陈有福是我和侯加昌共同的偶像,也是那一代羽毛球爱好者们共同的记忆。1956年,19岁的陈有福横空出世,成为世界羽坛的一股新鲜力量,世界羽坛正式进入快速、凌厉、激烈的现代竞技时代。
对我而言,他的球技球风、品学教养以及在成为印尼“国家英雄”后依然没有放弃中国国籍的恋祖爱乡之心,都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未曾预料到,能作为一名中国羽毛球运动员,与他在球场上相遇。
广州是印尼队访华的第一站,1964年6月22日晚,广州体育馆座无虚席,在5000多名观众的注视下,我和队友黄鸿平对战陈有福和乌南,以1:2告负。几天后,我在单打上遭遇了印尼名将汪百胜,第一局我以15:10获胜;第二局我越战越勇,打出了一个15:0。多么巧合的一个数字,在人生的第一场羽毛球赛上,我曾输在了同样的数字上;而那天,我以同样的比分赢得了比赛。我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对得起父亲的期盼。
在随后的北京赛,由于黄鸿平身体不适,我和侯加昌作为中国国家队选手临时搭档,组成男子双打迎战陈有福和乌南。我们兴奋而幸福着,更是沉下心,让这对印尼王牌双打在此行中首次尝到了败绩。
在北京,中国羽毛球队最终以4:1战胜了印尼国家队,我和侯加昌以出色的发挥致敬了心中的偶像;困难时期艰难成长并壮大的中国羽毛球队,更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实现了贺龙元帅提出的“3年打败世界冠军”的目标。
我们做到了!
“
因为腰伤和膝盖伤,我已遵医嘱,多年不再打羽毛球。路过球场时,就远远看着,也是津津有味的。
伤痛会伴随着运动员的一生,我也没有例外,只是有遗憾。
因球结良缘
回国时,我孑然一身,一腔热血只为心中的羽毛球梦想和中国羽毛球事业。幸运的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收获了人生的宝贵经验与财富,还找到了知己和相伴一生的妻子。
 ▲傅汉洵夫妇近照
▲傅汉洵夫妇近照
我的妻子曾秀英祖籍福建,是马来西亚归侨。1960年我正式加入广东羽毛球队时,她已经是一名“老队员”了。在生活与训练中,她对我悉心帮助;慢慢地,我也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这个直率、刻苦、勤快的姑娘。
感情何时萌芽,什么时候“走在了一起”,都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我们会一起从队里出发,走到广州市人民中路的一栋旧楼里,去探望她父亲的好友——李挺一。李公公(秀英称)一家居住的房间拥挤逼仄,却总愿意留我们在家吃饭。他是秀英“娘家人”中,第一个认可我们关系的。
在队里,我们却成为了生活检查会上的“靶子”,常被要求做自我检讨。可我们觉得“冤枉”,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只是有了好感,在生活中有更多主动的接触,相互关心而已。秀英脾气直,她挨的批比我还多。
1970年五一劳动节,我和秀英终于结婚了。那年年初,我们步行到射击场的一座两层楼下,楼中有几间空房,秀英看到广州市体委人事处处长毕敬清,就问道:“毕处长,这些房子能不能住人呀?”“能呀,你要不要?”毕处长笑闹着说。“要!当然要!”秀英迅速回答。毕处长认真了起来,让我们以结婚的名义打报告,很快获批。我们终于有了单独的住房。

▲全家福
尽管那是一楼的一间空房,几乎没有家具;尽管睡的是4条长凳架起的一张床板;尽管那里颇为荒凉,蚊虫多,但那是我们的家,我们在那里拥有了2个女儿,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遗憾转场
1969年,广东羽毛球队训练恢复,我欣喜不已,准备大展拳脚。可1970年下半年开始,腰部疼痛逐渐严重,后来下肢也开始发麻、疼痛。医生说,我的身体无法再承受大运动量的训练了,如果继续坚持很可能导致瘫痪。
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生生地砸在我脑子里。父亲的期望,家人的骄傲,我的梦想、汗水、努力……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成了空。时也运也命也,我最终还是没能站在国际羽毛球大赛的领奖台上。我痛苦了整整三天三夜,最终只能接受现实。

▲傅汉洵在训练馆内向学员讲解步伐。
那时,妻子筹办的广州体育馆体校羽毛球班正缺人手,在心爱的羽毛球面前,别的选择都无法抗衡。我最终还是和妻子搭档,加入创办广州体育馆体校羽毛球班的行列。时代不同了,或许在下一代的身上,我们这一代未竟的梦想可以实现!
那时羽毛球还是“贵族运动”,普及率很低,在广州几乎找不到有羽毛球基础的少年儿童。我与妻子只要有空就往小学跑,重点针对此前广东羽毛球队发展过一批对羽毛球运动感兴趣的中小学体育老师们。后来,我们常去的几所学校都成为了广州市具有羽毛球特色的学校。

▲小运动员们在傅汉洵家做游戏。
那时,每周一天,老师们来到体育馆接受培训,再回去向孩子们传授。老师们会将体育馆练坏的残旧羽毛球捡回去,给学生们练习使用;后来还听说有的老师动员孩子们从家里拔鸡毛、鸭毛,以修补残坏的羽毛球,为此甚至惊动了家长,担心孩子们是要做什么坏事,急忙前去了解。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况是从小的耳濡目染。几十年后,羽毛球运动在广州蓬勃发展,广州成为世界羽毛球顶级赛事“大满贯”第一城,良好的群众基础和运动普及率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1973年,广州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成立,羽毛球是最早的项目之一,我与妻子是第一批羽毛球教练。广州原五十六中的礼堂被安排为羽毛球和乒乓球的训练馆。那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礼堂,水泥地面粗糙不平,头顶的石棉瓦“弱不禁风”,门窗破败,冬日里冷风呼啸而入,还能在里面打旋儿。
 ▲傅汉洵悉心指导中心体校学员。
▲傅汉洵悉心指导中心体校学员。
校方在我们的要求下,“修理”了门窗:将窗户都封了起来,原大门找回,勉强维修使用。到了夏天,不通风却装着大功率灯泡的礼堂就是一个“蒸笼”,广州酷热天气下,馆内温度可达40℃。
我们就在这样的训练馆以惊人的意志力坚持着。1975年夏天,时任上海羽毛球队教练蒋永谊专门来广州,想向我们“取经”。他来到礼堂后简直傻眼了,才几分钟他便汗如雨下。他认真地问我:“你们就在这里训练?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可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在全国同行中脱颖而出,向许多专业队伍输送了人才。甚至在1977年全国青年羽毛球赛团体赛上,依次战胜了上海、福建和湖北等6支专业队伍,成为赛事上的一个特殊“现象”。1978年,全国业余训练和推行《国际体育锻炼标准》工作会议举行,我与另外3名体校教练员一同获得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978年,国家体委原主任王猛(右一)与获颁“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的傅汉洵(左二)握手。
1978年12月,由于我们的出色成绩,广州市正式获批成立羽毛球队,这是全国第一支市一级专业羽毛球队,它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国际赛事”再立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门敞开,我与汤仙虎、林丰玉受国家体委指派赴澳大利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羽毛球教学。在第一站帕斯,当地羽协官员接待我们的时候,态度傲慢轻怠。在第一节课上,羽协官员表示,他们平时也有印尼的教练带队,不知道我们的水平与他们相比如何,希望我们与曾是印尼国手的两位教练来场比赛。
彼时我因腰伤已退役多年,汤仙虎也正逢身体不适。但大局面前我们毫不怯场,说打就打。于是,中印两国的前国手在澳大利亚帕斯“狭路相逢”。这荣誉之战我们打得很激烈也很过瘾,最终击败了对手。这看似一场简单的比赛,却是我们退役后的一场国际比赛。我们再一次为国争了光;更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羽毛球运动员“无冕之王”实至名归。

▲1983年,傅汉洵教练与新加坡国手黄循杰及队友的合影。
后来,我还被指派到新加坡执教,并助力新加坡选手黄循杰在1983年第十二届东南亚运动会上击败“世界羽坛霸主”印尼队的多名选手,夺得新加坡在东运会史上第一枚羽毛球金牌。据说,这是新加坡羽毛球馆建馆50多年来,第一次有本土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主场夺冠。那天,为了这次胜利,他们史无前例地奏响了3次国歌。我与有荣焉。

▲傅汉洵赴新加坡时,被寄予厚望亿万28。当地华文媒体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
2003年,我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作为教练的羽坛生涯就此结束。在我和秀英培养的运动员中,产生了6位世界冠军(其中1名奥运冠军)。父亲对我的期望,对中国羽毛球的期待,幸而在他们的身上都一一实现了。

▲1985年,获得尤伯杯后,傅汉洵夫妇与爱徒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的合影。
我从印尼漂洋回来,为之拼搏了、奋斗了、见证了、更成就了,其间有无数血汗、有刻骨遗憾,有至上感动与激情,有友情、爱情、亲情……此生何其有幸。
☞参考资料:傅汉洵/口述 刘晨/整理:《赤子情·羽球魂——傅汉洵回忆录》,南方日报出版社。
编辑丨郝兆嵘
审校丨廖慧敏
编委丨林萧凡
✎本文 来源于福建侨报,转载请注明来源。
✎邮箱 来稿邮箱:xcc@chinaql.org
长按二维码,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中国侨联” ↓↓↓


觉得“好看”,请点这里
发表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来抢沙发吧~